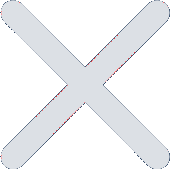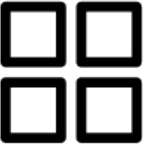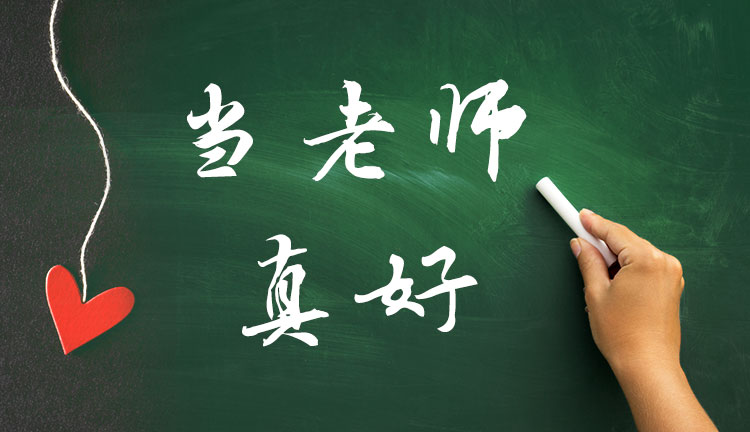
ADVERTISEMENT
宋代人喜歡杜甫,把杜詩神化到“無一字無來處”,非得有豐富學識不能讀。就連大臣上朝,也會趁隙談杜詩。其中有個吳姓官員,常纏著葉濤談杜詩。葉濤很不耐煩,皇帝還沒上朝,他就搬凳子到外頭坐。有天下雨,他也不避,人問其故,他說:“怕老杜詩”。
我談“母語教學法”也近十年了,某天古校長便對我說:“講座上半場很好,下半場我忘記提醒您不要講母語教學……”呵呵,我馬上聯想到葉濤。
自當老師以來,我從不用舊講義。每一次演講,乃至課堂每次教學,我都會重新組織材料。如此螺旋式的學習,才會確保教學相長。由於收集課後反饋,對聽眾的異見或不解之處,我會再去發掘新材料,以補之前的不足。實踐和理論結合後建立起來的知識結構,不見得討好。一是難以取信學術界,二是不易說服只管聽從指示行事的教育工作者。
我還是學生的時候,就感受到華文作為學科不為大家所喜愛,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如此。中學同學大多都選擇放棄報讀。早期我讓師範生去調查小學生最喜歡的科目,結果首選華文的人數只有逐年下降。
我的“母語教學法”就是立基於這樣的觀察而提出,雖沒有一家之言的意圖,卻也致力窮究人天之際,以通古今之變。
這期間發現我們的社會有妄自菲薄的趨向,常認為我們先天不足,後天又失調,所以反對把華文作為母語來學習。先天不足我是同意的,後天的努力不是比失調更好嗎?我到南京留學,先天不足的感受更加深刻,卻因此發奮圖強,儘量看古籍,看學術報告。結果答辯時,主席即席宣佈他要他那和我同題的博士生換題目。
目標明確、方法得體、環境得當,一切將化為可能。這三者不是師者所能提供的嗎?為什麼我們對兒童不加多幾分的尊重,對未來不抱多點幻想,憧憬明天會更好,寧願畫地自牢,自我設限?
#
ADVERTISEMENT
热门新闻





百格视频





ADVERTISEME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