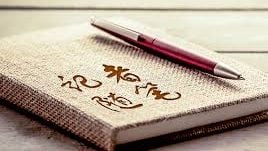李秀云 | 那一扇铁门的距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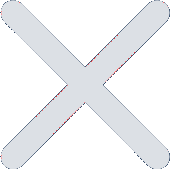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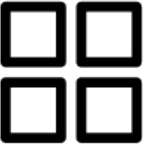
1961年,政府颁布《教育法令》,推动华文小学的改制,随后到了1969年,中华学校顺势而行,正式将小学与中学分设为两个单位:中华小学、中华中学,而后来又发展出中华独中。
3所学校,名义上分家了,可实际上大家依然共用着同一片校园。
ADVERTISEMENT
我正是那段历史变革下的学生。那时的中华学校,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家庭。低年级的我们在中学的教学楼上课,高年级则转入小学的校舍。
小学升中学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,不需申请,不需考试。校园里的每个角落,无论是草地、食堂、图书馆,甚至体育馆,大家轮流用、一起守,仿佛没有界限。
不管是下课时段,或者是放学的时候,都是学生们的快乐时光。他们会奔跑,也会呐喊,甚至是做出违反的行为。
当然,也会造成彼此的不适,甚至是互相指责。其实,都是学生,人数众多,也难控制。然而,校园却是学生的第二个家。如果他们没有在熟悉的环境里玩乐,那么他们会去哪里呢?
球场,是我们最多回忆的地方。无论是跳格子、打篮球、追逐松果,我们把青春写进了每一块砖石。可如今的孩子玩耍的最多的,是手机屏幕。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中小学之间筑起了一道墙。那一道墙很简单,底部是钢骨水泥,差不多3尺以上,再用铁条围起,末端还很尖锐,是为了防止中学生翻墙,但也可以看到对方。
铁门旁边,挂着写着“未经允许不得进入”的告示牌,像是一个冷漠的指令,把我们从一家人,变成了两个单位。
就是这样,中小学生只能在各自的校园活动而已。中学生也不能在小学毕业后,开心地跑回小学篮球场打球。偶尔还因为身体长高了,可以跳跃灌篮了;小学生也无法跑到中学的草场玩乐,或者在走道上拾起掉落的松树果子。
从此以后,中小学就分道扬镳了。
可是小学的图书馆还在中学校园内,而且食堂就在图书馆楼下。小学生必须经过一扇铁门,走入中学校园里。中学生放学后,也会经过那扇铁门,穿过小学的校园,走到另一条马路,回家、等巴士、去托儿所、吃午餐等等。
每天看到的,都是熟悉脸孔的学生,因为中小学都是大家的学校,不分彼此!可是,那一扇铁门,却让我们分隔得更远了。
后来,疫情爆发了。虽然学校重开,可是铁门紧闭。每一个学生都被圈在自己的校园里,只剩下特定人士可以自由通行——譬如老师的孩子, 老师却要在门口站岗。
疫情稍微缓和,铁门开始定时开放。可我永远记得那天下午,倾盆大雨,我在小学等待在中学的孩子。可是铁门却关着了,孩子也无法走过来。当时候我只是觉得,孩子会不会冒着大雨,然后绕道到小学的校门?
可是我也想起,不只是我的孩子,还有我的学生。我把所看所思写在脸书上,也因为这一扇铁门,我毅然选择提早退休。
一扇门只是开始而已,后来也因为一个球的连环故事,我选择了安静离开,不再踏入小学校园了。
可这里的一草一木,仍旧烙印在心底。那些我们曾共用的体育馆、食堂、草地、松树下的落果,还有那道曾经敞开、如今紧锁的门……是我教学生涯的缩影,也是我一代人对学校的记忆。
那是一道铁门,也是一道时代的墙。
ADVERTISEMENT
热门新闻





百格视频





ADVERTISEMENT